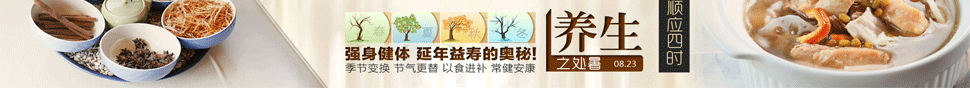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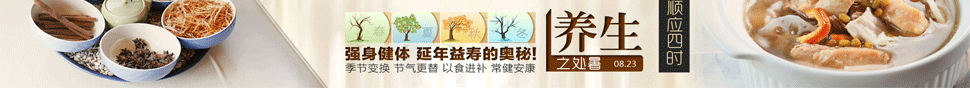
偏花报春、锡金报春,一山谷接着一山谷。
云南杓兰、黄花杓兰、西藏杓兰、离萼杓兰。
绢毛蔷薇、细梗蔷薇。
绒舌马先蒿、蒙氏马先蒿。
大白花杜鹃、云南杜鹃、黄杯杜鹃、红棕杜鹃、多色杜鹃、金黄杜鹃、栎叶杜鹃、樱草杜鹃、雪层杜鹃。
川滇雀儿豆。金铁锁、匍茎百合。
中甸刺玫、中甸菠萝花、中甸山楂。
云南丁香、云南山梅花、云南银莲花、云南耧斗菜、滇牡丹。
景天点地梅、刺叶点地梅。白花刺参、红花刺参。
独丽花、少花虾脊兰、龙舌兰、腋花扭饼花、管花鹿药。
倒提壶、驴蹄草、凉山悬钩子、岩须、红花岩梅、洼瓣花、狭叶委陵菜。
粉背玉凤花、长苞头蕊兰、唐古特忍冬、西南鸢尾、玉龙蕨、桃儿七、小山兰。
叶日村的梨果仙人掌肥美、硕大,两三米高,冠幅两三米。
叶日小道上的绣球藤攀附着华山松、高山松、大果红杉,一直长到二三十米高。
茄参,有毒,据说欧洲那些话多的哲学家,大多被赐服茄参属植物而死。
川犀草——中国只在奔子栏对岸的得荣县瓦卡镇一带可见,长在金沙江边,四五月开花,然后死去,待六月洪水过境,淹没生长区,种子便由洪水带到下游沿岸。
「史诗级绿绒蒿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史诗之旅」是真的,但只是由绿绒蒿打头阵,后面跟着百余种、数百种其他高山野生花卉。此刻,夜里十点的飞来寺,缅茨姆峰带着垂直海拔近千米的黑色森林,长卷一样横在窗外。这是我们的银色旅程。▲旅途是这么沿着一座座山、一条条沟谷、一坡坡流石滩,逐一展开的。绘图/刘欣6.22.我的羊群,今天整日放养在普金浪巴山谷。见桃儿七,一整山坡。五年长成,花开四日,我们有幸与她相逢。
横断山绿绒蒿漫山遍野,我们先是驻足凝视,然后在她旁边过林卡,再然后,因为太多,视之为“杂草”,视而不见,过而不停。
见美丽绿绒蒿的幼芽、花苞,和两年前留下来的完整枯枝。
见川贝母、梭砂贝母。落新妇、黄秦艽、岩白菜、绢毛苣、红花岩梅、滇边大黄。
冻地银莲花、宽叶变黑蝇子草、水母雪兔子、四裂红景天、大花红景天。
多脉掌叶报春、锡金报春、紫花雪山报春、雪山小报春、山丽报春、锡金报春、偏花报春。
囊距紫堇、浪穹紫堇、暗绿紫堇、灰岩紫堇。
矮金莲花、唐古特瑞香。
拟耧斗菜、线叶丛菔、欧氏马先蒿。
往年常见的总状绿绒蒿、宽叶绿绒蒿、长叶绿绒蒿、轮叶绿绒蒿,因为物候推移,今年都没见到开花。
我们解剖狼或者狐狸留下的一坨屎,里面留着朱雀的爪子和旱獭的毛。也解剖一坨福禄草,这一坨,保温、保水,使自己完美适应冰缘带的寒旱逆境,也庇护其它植物——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她以自己为背景,供十余种植物栖居其上。在草甸上、石头上、溪水边,我们在任何地方坐下,听长风浩荡,听牛铃混入山溪里,听风抚弄经幡。黑耳鸢从头顶飞过,牦牛在对岸山坡徜徉,喜马拉雅旱獭钻入岩石下。我们坐下,看风推着云,云推着光,在海子、流石滩、月球般的山脊上不疾不徐地优雅移走。生态摄影师彭建生在海子边高唱“阳光走路的声音,格桑花听得见。月光落地的声音,卓玛听得见。”而植物学家徐波在一旁设想,如果使这些冰缘带植物、使绿绒蒿进入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会怎样呢?比如,油纸伞里绘一朵美丽绿绒蒿,雨水里撑开伞,一朵美丽绿绒蒿就在头顶绽放。我们撑着这把伞,走在通往云里的山路上。▲普金浪巴冰山一角。摄影/彭建生黄菊6.23.终于站在了怒江边,它巨大,混浊,刚刚淹没过公路和村子,但终于站在了它身边,怦然心动着。整宿开着窗,让江风穿过茂密的核桃林,穿过清晨的鸡鸣和白雾,一缕一缕吹拂我们。昨天横切了一段怒山山脉,翻越孔雀山垭口,才从澜沧江来到怒江边。沿途见瀑布千百条,从浓黑的森林里一条条淌下。除非你来到她身边才听见巨大的轰鸣声,大多时候,只见千百条细长的白练从黑色森林里安静淌下,一折,三折,随着陡峭感受着十数次转折后,才从雪线下穿过云杉、冷杉、大果红杉、澜沧黄杉和杜鹃林,来到脚下。植被的丰盛,道路的险绝,使我们眩晕,最使人眩晕的,是中高海拔地带一段浓雾遍布的白桦林,站在那里,除了想起阿巴斯的诗,身心俱空:白色马驹,浮出雾中。转瞬即逝,回到雾里。今日见两头毛、香柏、侧柏。拟耧斗菜、云南大百合。
大果臭椿、澜沧黄杉、常春藤、德钦杨、滇藏槭。
突尖杜鹃、魁斗杜鹃、似血杜鹃、弯柱杜鹃、川滇杜鹃、紫背杜鹃、樱花杜鹃、平卧怒江杜鹃、粉红滇藏杜鹃、多变杜鹃。硫磺绿绒蒿、滇西绿绒蒿。
春花脆蒴报春、苣叶脆蒴报春、长柱独花报春、大叶雪山报春、美花报春、独花报春、齿被灯台报春。
暗紫贝母、高山捕虫堇、岩须、黄三七、圆叶点地梅、云南丫蕊花、贡山贝母兰、四照花………
▲白色马驹,浮出雾中。转瞬即逝,回到雾里。摄影/黄菊6.24.越过左侧的草甸,越过天际线的石山长卷,一小扇薄如蝉翼的雪山,从透明和空无里浮出来。走过那么多雪山,即使她旁边就是卡瓦格博王者般的背面(西面),但站在益秀拉垭口,瞬间被海拔只有多米的木孔雪山击中,从此成为心中最爱的雪山。丙中洛经察瓦龙到目若村,一天长卷,全程高潮。而让舍曲谷地是杓兰的天堂:黄花杓兰、宽口杓兰、无苞杓兰、褐花杓兰、西藏杓兰,布满整个山谷。但经过前几日的见识,我们已经膨胀到除了目标物种,其余统称为“杂草”,无非客气地加个定语,“顶级杂草”。▲此次旅程见杓兰12种:离萼杓兰、宽口杓兰、黄花杓兰、高山杓兰、紫点杓兰、西藏杓兰、褐花杓兰、云南杓兰、无苞杓兰、雅致杓兰、波密杓兰。一山接一山,以上仅是冰山一角。摄影/徐波叶茂等
6.25.丙(丙中洛)—察(察瓦龙)—察(察隅)之路就是杓兰之路:在昨天的几种杓兰外,今日又在目若附近的河谷新见雅致杓兰、无苞杓兰、紫点杓兰、高山杓兰,如繁星,缀满一山又一山的林下。大雪纷飞里,雄珠拉垭口远看空无一物,只是黄褐色的碎石坡,但走近、趴下后,简直繁花似锦:滇西绿绒蒿、雪兔子和暗绿紫堇,以梦幻般的紫色、翡翠色,密布其上,应接不暇。拍累了,那就躺下,淋着雨,吹着风,像她们一样,沐浴着流石滩,看雪山横亘天际,看浩浩荡荡的山谷左右交织着越推越远。杓兰外,今日见紫花百合、中甸灯台报春、象鼻南星、腋花扭柄花、管花鹿药、多变杜鹃、雪层杜鹃、喜马拉雅岩梅、车前叶雪山报春、紫晶报春、冰期孑遗物种桫椤、贡山棕榈、川百合、叠鞘石斛……等“顶级杂草”百余种。
两天,三座山,边境盘查五六次,终于走完险绝的丙察察之路,察隅到啦。▲流石滩就是这样,远看荒芜一片,近看繁花似锦,如果你不走进,不跪下、趴下,也就擦肩而过了。摄影/叶茂
『植物人类学』察隅出发,溯桑曲河而上。桑曲河翻滚,两岸森林浓黑,直至德姆拉垭口,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逐渐向温带高山松林过渡。这一程,反反复复从干热河谷切到湿热河谷,从低海拔爬到高海拔,植物以放映幻灯片般的速度切换着,前一刻还荒凉着,一拐弯便丰盛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我们每次观花的高潮都在垭口,又是怎么回事呢?从尾车向头车发射问题。行李徐波黄菊:呼叫徐老师。想知道,一个区域,一座山,植物的丰富性和什么关系最紧密?徐波:简言之,“昨天、今天、明天”。“昨天”是指地质背景,如果经历过大的冰期,像北美、欧洲,就会大大减少物种的多样性,但喜马拉雅山脉是地质史上新隆起的区域,高大山体的隆起,触发了物种的辐射演化,这里的高山植物多样性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再说“今天”,我们途经的这个区域,气候、水热条件比较理想;加上山地环境,像今天,我们会从海拔多米的察隅爬到海拔米的德母拉山,从河谷到山脊,会看到很多物种的变化,现在看出去有高山栎、黄背栎在内的很多乔木,随着海拔上升,乔木越来越少,就会出现高山松、落叶松,然后是冷杉、云杉等。还有人的因素,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世居民族相对温柔,物种的多样性保持得非常好。对同一座山而言,物种最丰富的是中高海拔地带,大约在-米区间。一个原因是,河谷相对狭窄,不像高山,视野开阔,面积也大。人类也居住在低海拔区域,会利用、破坏,物种相对单一;另外,这里介于高海拔和低海拔之间,是一个过渡性区系,区系类型多样。当然还有“明天”的因素,就看这个地区未来能否保护好。黄菊:不知道有没有类似“植物人类学”的学科?做“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区域的人类学研究而不涉及植物,或者相反,研究植物而忽视这个区域的民族,感觉都会出现一些空白。徐波:目前国内还没有?但我特别感兴趣。东西方植物学家在这个区域的活动都很重要,西方的多少有些记载,中方的资料特别少,很多都散佚在老一辈学者的日记里,这个工作量浩大,相当于是植物考古学,但随着他们的离去,资料没人整理,这些历史也就不在了。第一个进入青藏高原的植物学家,我认为是刘慎愕,一个非常传奇的东北汉子,不要命那种性格。没记错的话,他是最早去法国留学的一批学生,后来回到中科院东北农林土壤研究所。早期没有植物所,植物学家都放在农、林系统里。建国初期,各国封锁中国,那时科学家有气节、有使命感,不为名不为利,所有工作都围绕着为国家寻找资源,国家需要野菜,需要粮油,需要橡胶,这些人就努力寻找替代资源。刘慎愕从北京出发,一个人,一路向西,抵达新疆,当时西北非常乱,一路遇到很多土匪,被劫、被抢,但他一心想收集标本,最后辗转多地,从阿里地区进入到印度(那个年代中印关系相对友好),因为出去时间太长,又杳无音信,大家都以为他不在了,后辗转香港等地回到东北,非常传奇的一个人。刘老对中国植物学界做过很大贡献,中国最早的一批植物志,《东北草本植物志》、《东北树木植物志》都是刘慎谔先生完成的,略薄的小册子,后面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等专著,多有借鉴,所以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非常了不起。还有许许多多植物学前辈在此默默耕耘过,他们不应该被遗忘。黄菊:看植物,如果能沿着这样一位植物学家的足迹重走,多好。徐波:刘老的考察之路在整个中国植物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很多人对他了解不多,我是从标本里看到的这些历史信息。黄菊:一个人和他的研究对象完全融在了一起。和徐老师一起走过,你,你的前辈,你们这些植物学家的生命就注入了我们体内,也对我们的生命构成映照。徐波:和喜马拉雅互相影响的植物学家太多了,我经常说起的是日本学者吉田外司夫,70多岁还在坚持做野外调查。吉田先生相继发表了10余个绿绒蒿新种,很多人吐槽他发布的一些小种不成立,我认为部分种是成立的。因为他的很多标本存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KUN),部分标本是我处理的,这些绿绒蒿在野外的植株群落我见过,比如夹金山绿绒蒿和总状绿绒蒿的区别在花蕊上:雄蕊内部花丝特化,包裹雌蕊,这跟其他绿绒蒿完全不一样。很多人没见过,我在野外做过细致观察,有特写的照片,是成立的。吉田先生非科班出身,能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错了。吉田先生是世界上唯一走遍喜马拉雅南、北坡的人,以前,现在、未来,都不会有人超越他。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人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的特殊人才,吉田先生是其中之一。最开始研究社会意识形态,后面对喜马拉雅地区的高山植物产生感情,渐渐从一个外行转变成专家。他喜欢自然摄影,获得资助后,一个人,从喜马拉雅南坡走到北坡,历经千辛万苦,最后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就是《喜马拉雅植物大图鉴》,那是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我努力一辈子也超越不了,因为那时中印之间正处于蜜月期,喜马拉雅两侧相对开放,以后不可能了。吉田先生语言能力较强,平日是带着锅碗瓢盆搭老乡的摩托车,进到山里住下,然后开始调查的,他在中国藏区调查路线,很多区域至今无人涉及,也难以触及!喜马拉雅南坡我是不可能走遍了,只能尽量走完北坡。吉田没去过珠峰东坡,我去了两次,给他看照片,他很感动,说“我老了,去不了了。”但北坡我还有几个区域没去:扎日神山、希夏邦马、冈仁波齐、喀喇昆仑等,这些都写在我未来的计划里,都是无人区,植物调查严重匮乏的区域,都要徒步,趁身体好、腿脚灵便的时候,想把这一圈走遍,经费充足的情况下,至少还得三五年。但没经费,想都不要想了。▲“海拔越高越膨胀”的流石滩滩主,被大家昵称为“波波老师”的徐波。摄影/叶茂日记·『藏东南的两只犄角』6.26.翻过益秀拉、雄珠拉、昌拉,终于来到德姆拉,这是上世纪70-80年代中科院青藏队采集标本的地方。见横断山雪莲、岩须。大面积的滇西北点地梅、圆叶点地梅、喜马拉雅岩梅、独花报春、山丽报春。葶菊、大花红景天。尖被百合、小百合、黄花小百合等等。
一过垭口,仁龙巴冰川就挂在眼前。冰川淌出了冰川河,冰川河在舒缓的德姆拉草原淌出了辫状水系,我们在水系旁的杜鹃林里流连忘返。下山,过然乌湖,来古冰川流出了帕龙藏布,雨水使帕龙藏布河谷有了“阴翳礼赞”的隽永之气。顺江而下,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一路到波密,这是中国森林最完美的区域,真正的完整森林:山顶是连绵不断的雪峰,雪线下就是寒温带暗针叶林,森林和冰川“十指相扣”。6.27.嘎隆拉岭徜徉一整日。见紫背杜鹃(红色)、弯月杜鹃(黄色)、弯柱杜鹃(暗红)、杉叶杜。
乳黄雪山报春、中甸灯台报春、长果报春、西藏独花报春、察日脆蒴报春。
叶萼龙胆、胡黄莲、林芝凤仙……
6.28-29.在色季拉迎来绿绒蒿的高潮:硫磺绿绒蒿、单叶绿绒蒿、滇西绿绒蒿、拟多刺绿绒蒿、普莱氏绿绒蒿、百利氏绿绒蒿。
以及塔黄、绵头雪兔子、苞叶雪莲、宝璐雪莲、金东雪莲。
小百合、钟花韭、条裂垂花报春、不丹兰、大花红景天。紫花虎耳草、腺瓣虎耳草,
以及这一程的第十二种杓兰:波密杓兰,有乳黄、暗紫两种颜色。
换一条牧场小道,又见另一片花海:
比比皆是一两米高的塔黄。大花韭、单头尼泊尔香青、杂色报春、暗紫脆蒴报春、林芝报春。
以及数量更多的拟多刺绿绒蒿、普莱氏绿绒蒿、百利氏绿绒蒿、单叶绿绒蒿、硫磺绿绒蒿、滇西绿绒蒿。
在米的山口,徐老师讲植物在高处生长的智慧,巴掌大的岩石下,共生着十余种植物:绵头雪兔子、绢毛苣、垫状点地梅………去年、前年死去的枯枝和腐叶,会继续留在植物基部,用以保暖、保湿;倾斜的石缝渗下雨滴,也供大家一起享用。走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让舍曲、桑曲、帕隆藏布、易贡藏布、帕隆藏布,终于走到雅鲁藏布江边。此刻,历经洪水、泥石流、塌方、雪崩、边境检查、疫情防控………总算到林芝啦。6.30.整日多雄拉岭观花,徐老师前一晚提醒:山上有暗红紫晶报春、翅柄岩报春、镰叶雪山报春、裂叶脆蒴报春、小花灯台报春、林芝报春、杂色钟报春、菊叶穗花报春、暗紫脆蒴报春、条裂垂花报春、中甸灯台报春、展瓣紫晶报春、暗红紫晶报春、腺毛小报春等20多种报春。
以及林芝杜鹃、藏布杜鹃、弯果杜鹃、毛喉杜鹃、云雾杜鹃、雪层杜鹃、矮小杜鹃、半圆叶杜鹃、多花杉叶杜。
锥花绿绒蒿、单叶绿绒蒿、百利氏绿绒蒿、美丽绿绒蒿。
还有贡山蓟、苞叶雪莲、大花红景天、多榔菊属、叶萼龙胆。
尼泊尔香青、无茎荠、喜马拉雅岩梅、腺瓣虎耳草、小百合、腋花扭柄花。
跨过近百米的积雪陡坡,再穿过密布的杜鹃林灌丛,爬到垭口。十二年前来墨脱徒步,翻过这个垭口,下面就是拉格、汗密、背崩。整个青藏高原,论高山植物的丰富度,嘎隆拉、多雄拉山是最殊胜的山头,她们像两个犄角,挂在滇西北—藏东南的拐角处,挂在墨脱的东、西两端,而徒步进墨脱的人,一如十二年前的我,又对这两座必经的山脉知道多少?▲益秀拉、德姆拉、嘎隆拉、多雄拉、色季拉……一拨接一拨的观花盛宴,在一个接一个的垭口应接不暇地展开,垭口是接引人类抵达冰缘带的窗口。摄影/徐波彭建生叶茂『绿绒蒿垭口之恋』物候每年都在变化,往年绿绒蒿开花最盛时,桃儿七、杓兰等林下植物就见得少,今年相反。这正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课堂,除了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左右。旅途走到一半,徐波老师用一个傍晚的时光,和大家分享他遇见的绿绒蒿。目前公认的绿绒蒿,全世界80多种,中国70多种,他记录了46种。几天后,他将迎来他的第47种绿绒蒿。行李徐波黄菊:我第一年来看绿绒蒿时,以为就一种(捂脸),进来后才知深似海呀。你是国内见绿绒蒿种类最多的人了吧?徐波:国内从事绿绒蒿属研究的学者很多,他们见的绿绒蒿可能都没有我多,因为我跑野外够多、够远。虽然记录了很多绿绒蒿,但对它的认识仍然很肤浅,现在我更愿意坐在它旁边,摸一下,闻一下,从触觉和嗅觉上,增加彼此间深层的交流。像康顺绿绒蒿,比较罕见,见过的人比较少。深红色的花朵颜值很高,她的刺毛细长细长的,植株可以到腰间,一米多高,在冰缘带上很霸气。如果坐在石头上,她和你一样高,风吹过来,晃来晃去,就像和你聊天一样,那感觉很棒。如果只是隔着相机、手机和电脑的屏幕看照片,永远体会不到这种美。黄菊:为什么这么爱绿绒蒿?徐波:高山冰缘带有很多特殊的植物和优势类群:虎耳草、报春、乌头、雪兔子、雪莲、紫堇、翠雀、垂头菊、丛菔……但绿绒蒿太特殊了,对全世界的花友来讲,喜马拉雅地区最著名、最吸引人的植物,一定是绿绒蒿。绝大多数绿绒蒿都是多年生长,但一生只开一次花,结一次果,然后死掉。绿绒蒿花色多样,吸引路过的人们驻足欣赏、赞叹,但有毛或刺,这是一种抗拒的美,人往往对这种抗拒的美充满无限期待。黄菊:那怎么没有以绿绒蒿为研究重心?徐波:一直很想做这个类群的研究,但国内外已经有很多人在从事绿绒蒿属研究,想一想,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爱好吧。黄菊:所有绿绒蒿都很难见到吗?徐波:不是,像全缘叶绿绒蒿、红花绿绒蒿在川甘藏区就如杂草一样的存在。也很多绿绒蒿我还没见到,但我知道长在哪里,而且很多,比如贡山绿绒蒿,在独龙江数量之多,就是路边的“杂草”。还有威氏绿绒蒿东方亚种,我找了两年,一直没找到,其实就在昆明的轿子雪山景区。我拿着照片问接待中心的大姐有没见过,大姐很不耐烦,窗户一推,一瓢水泼出去,很不屑地说,“喏,你看!”就在她厨房外,每天炒菜后洗锅,都会把洗锅水泼两瓢出去,就泼在绿绒蒿上。黄菊:你常批评我们在野外拍些“杂草”,原来绿绒蒿也会被视作杂草。徐波:“杂草”是玩笑,植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如果在家门口就可以拍到,为什么跑这么远的地方来拍?在每个地方,都应把最宝贵的时间用在特定的物种上,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在轿子雪山,目标之一就是“杂草”威氏绿绒蒿东方亚种。黄菊:白马雪山垭口、孔雀山垭口、雄珠拉、昌拉、益秀拉、德姆拉、嘎隆拉、色季拉、多雄拉……我们这一路都在垭口观花,但白马雪山正对着更高的卡瓦格博雪山,孔雀山紧挨更高的碧罗雪山,嘎隆拉就在世界级的南迦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附近,为什么只在垭口看花,不去植被带更丰富的雪山呢?徐波:原因很简单,雪山太高,且远离公路,难以触及。山在垭口交汇,河在垭口分流,它是公路能抵达的至高点,又是山的低槽点,是高山冰缘带向人类开放的一扇友善的窗口,不必远行,也不必去雪山冒险,就在路边,触手可及。很多模式标本的采集点都注明采自某某垭口,如果没有垭口,普通大众就没办法了解冰缘带的植物。日记·『雅江河谷到喜马拉雅南坡』7.1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出发,整日溯雅江而上。途中见白腹短翅鸲、黑眉长尾山雀、西南鸢尾。见巨柏,主干几千岁,山上岩石几百万年,周边村子数百年,而我不到四十岁,站在这一切的中间……面对巨柏,感慨一棵树就是一座密林,一个古老的家族,一个珍藏了地质、气候变迁秘密的博物馆。藏族人用经幡、玛尼石、白塔、擦擦,想象它,装点它,和他倾吐心事。我们擦肩而过,匆匆一瞥,那就陪它坐一会儿吧,让山间的风,河谷的风,草坡上的牛铃,青稞地上的鸟叫,雅鲁藏布昼夜不歇的轰鸣,摇曳的经幡,陪我们一起坐会儿。7.2站在海拔米的垭口,俯身朝向拉姆拉错时,我们都哭了。击中眼眶的只是一面映照心性的湖水吗?还有环绕的荒凉群山。击中我们的不是湖水,也不是群山,是超越自我后的平静。我们消融自己,越退越远,不是退回内心,是退出自己。往返途中见:雪层杜鹃、金东雪莲、苞叶雪莲。
穗花报春、钟花报春,以及一种新的雪山报春。
瘦叶雪灵芝、密生福禄草、黄毛翠雀、昌都点地梅、垫紫草。
黄波罗花、四蕊山莓草、岩隙玄参、藏葱、大花红景天。
宽花紫堇、关节委陵菜、丽江马先蒿、拟耧斗菜、西藏铁线莲、珊瑚苣苔。
横断山绿绒蒿多如繁星,铺满了好几坡流石滩。以及数量不多的总状绿绒蒿、多刺绿绒蒿、拉萨绿绒蒿、拟多刺绿绒蒿。
还有灌丛里的旱獭、藏马鸡、藏雪鸡。
▲抵达神湖之路。摄影/叶茂7.3今日停车三次。第一次停在海拔处,见岩生银莲花、黄波罗花、西藏杓兰、白苞筋骨草、绒舌马先蒿、西南银莲花、狭舌多榔菊、高山绣线菊、刺叶点地梅、红花刺参、肉果草、紫点杓兰、马蹄黄、腋花马先蒿、某朱雀。
第二次停在海报米,见暗紫脆蒴报春、藏马鸡。
第三次停在海拔米的布丹拉山口,见丽江马先蒿、藓状马先蒿、密生福禄草、滇边大黄、昌都点地梅、山地无心菜、藏玄参、垫状点地梅、拉萨绿绒蒿(幼苗无数)、垫紫草(花开正好)、喜马红景天、垫状女蒿、高山丝瓣芹、唐古特雪莲、梭砂贝母。布丹拉的草甸啊,太过绚烂,无一寸土地没有花边镶嵌。▲布丹拉就是这么绚烂,这只是绚烂的一角。摄影/叶茂彭建生
7.5错那县到勒布沟,海拔在20公里的范围内急速下降多米,并从喜马拉雅北坡来到南坡,充盈的水汽扑面而来,道路似绝境,风光胜天宫,要怎么描述这一切呢?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就在你身边,所有房屋消失,所有声音褪去。左侧立起一道三千米的山峰,脖子后仰到底也看不见山顶;右侧也立起一道三千米的山峰,也是望不到顶。两道山峰之间,仅有一条翻滚的黑色江水,一条仅容一车通行的窄路。在河流拐弯处,两山可以握手。是石山,岩石坚毅,冷峻,因为薄,层层累积,因而兼顾秀丽。海一样的云雾在两山之间瞬息万变着,两道山峰无止境地迂回绵延着。几十上百条瀑布,从山的最高处,从云雾里,从每一道岩石凹陷的缝隙里,吹下来。注意,瀑布悄无声音,轻如云烟,比鸟的飞翔,风的抚弄,更轻盈,因为峡谷底部江水的轰鸣声,像风筒,吸尽一切声音。还要想象一下,这道峡谷,是从你此刻所在的地方,往上抬升两千八百米。左侧山外,一边是印度,一边是不丹。右侧山外,往上盘旋两千米,是六世达赖、诗人仓央嘉措青少年时,视野无数次抚摸过的广袤且肥美的草原,草原中间点缀着海子,草原的围篱是绵延的雪山。7.6锥花绿绒蒿、不丹绿绒蒿、单叶绿绒蒿,漫山遍野!漫山遍野!在这漫山遍野的几种绿绒蒿里,一位叫疤老叶的花友拍到了他当时并不认识,在晚饭的餐桌上才被徐老师认出的错那绿绒蒿!错那绿绒蒿呀(或称齿叶绿绒蒿),据说自从去年一个日本人拍到后,这可能是第一次被中国人用真实影像记录下来。于是,晚饭后,一桌人在暮色中重新杀回山上,她还安静伫立山中,而徐波因此拍到了他的第47种绿绒蒿。而我最爱藏南绿绒蒿,小小的、矮矮的、不多不少,安静地、平和地长在有水汽的崖壁上,我们攀爬途中无意中发现,先是一朵,再一朵,总计七八朵,疏密得当地点缀着一条不宽的空谷。纵有相机可以摄下其形,其色,可是那细雨、轻风、薄雾,那穿过漫山灌丛后忽然瞥见的发现的惊喜,那趴在崖壁上凝视她时的惊心动魄,那溪谷的湿润之气和轰鸣,也是无法记录下来的呀。▲除了错那绿绒蒿,在勒布沟,我们见到了数量上如杂草一般的锥花绿、不丹绿,乃至藏南绿。就是这样,漫山遍野,一坡接一坡。摄影/叶茂黄菊『标本高处生长的智慧』旅途中,徐波一直带着上、下两册厚厚的《横断山维管植物》,那是他做《横断山高山冰缘带种子植物》期间,最重要的参考书,书就放在车座底下,随时翻阅。还随身携带着的是每天换新的厚厚的标本夹,由“硬纸板+旧报纸+铁镐”构成,白天带大家看植物的缝隙采集,晚上回酒店答疑后再处理,往往后半夜才能完成,每天如此。行李徐波黄菊:现在已经有这么发达的拍摄技术,还必须标本么?徐波:标本的价值大于照片的价值,因为标本上能获得很多未知的特征。为什么要采标本,很多人不理解,如长果绿绒蒿是多年生,开花后还会接着开,我在同一份标本上可以看到年、年、年的果实,这就是证据。标本是关键的第一手资料,无标本依据的分类学是没有灵魂的。黄菊:采冰缘带植物标本在技术上有什么讲究吗?徐波:没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我一般能不采就不采,像色季拉、白马雪山这些相对容易抵达的地方,标本已经采得足够,调查也很清楚,就不必再采了。要采的话就尽量少采一点,尽量不祸害植物。冰缘带如果死一个物种,如绵头雪兔子,很多以它为家的昆虫也可能受到牵连。我坚持要去调查空白区域采集,冰缘带的植物,狭域特有种很多,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特有种,所以冰缘带采集的难处在于,要求每个山头都尽可能覆盖,不同的山头,不同的坡向,不同的季节,都有可能发现新物种。要了解这个区域,就必须做相应的调查。直观看,高山冰缘带海拔高,难以到达,工作环境残酷,很多高山物种的标本采集还不及三份,我们对它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研究这个区域的原因。黄菊:“死一个物种,很多以它为家的场所、平台也就不在了。”冰缘带看似荒芜,徐老师却一直用很热闹、聚集性的词描述,比如“平台”,你讲到吉田的照片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坨垫状植物,上面开了很多花,你说,那坨植物就像一个“小镇”。徐波:想象一下,周围全是流石滩,地表没有土壤,很多植物就没办法落地生根,但如果足够幸运,落到一坨垫状植物上,里边有水,还能保温,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经过生长,可以开花。我在色季拉山给你看过一坨密生福禄草,估计比我们行程里的所有人都年长,那一坨上,有蔷薇科、莎草科、禾本科、蓼科等植物总计十余种,都在福禄草营造的那个小环境里生存了下来。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下,大家都在争夺资源,它却表现出强烈的利它行为。冰缘带植物有很多特殊的适应结构,像垫状植物、温室植物、绵毛植物、垂头植物、隐蔽色植物等,各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在残酷异常的冰缘带上都发挥着各自的生态功能。黄菊:发挥功能,同时又极尽节约。记得你讲高山贝母时,说它的颜色,就在能吃饱(叶绿素用以进行光合作用)、又刚刚能保证自己安全(隐蔽色用以躲避天敌)的钢索上保持平衡。徐波:冰缘带的植物,有一些总体特征,比如花的颜色鲜艳,但也有高山贝母这样的隐蔽色;比如植株矮小,拍照时一定要跪下,不跪下,根本没办法发现它,也采不到标本,所以在冰缘带工作的人,膝盖和腿上肯定都有伤的;比如花和果的比例超大,作为营养体的叶子部分,所占比例非常少,但作为繁殖器官的花,非常大,在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会把所有能量集中在繁殖上,心无旁鹜。环境如此残酷,它没办法挥霍能量,一定很节约,即使枯死的叶片也会用来保护下面的幼芽、嫩叶,或者下一代。所以我始终认为,在自然界里,人要向植物、向自然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黄菊:“我读书很少,但一直在读的一本书叫‘自然’,其中一个充满智慧的章节叫‘高山’。”这些天总想起徐老师这句话,和你“流石滩滩主”的身份。徐波:经常有人问我去高原干嘛,说青藏高原植物区系那么简单,我劈头就问:你见过多少绿绒蒿?见过多少龙胆?见过多少报春?见过多少雪灵芝?青藏高原有20多种雪灵芝,很多人连5种都没见过,实际上这个区系非常复杂,存在大量研究空白。在国内,在学界,我肯定是爬流石滩最多的。从年开始,至今14年,一直在这个区域。像色季拉山,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来过多少次了,我爱人说,你把一座山都踩烂了,还去!?但反复来的魅力在于,可以重复累积观察。年复一年的来,不同季节来,对每个物种的生活习性都很了解,见证了她们从小到大的样子,也能理解她们高处生长的智慧。人有悲欢离合,但海拔越高时,我心情不会差。我常开玩笑说,海拔越高,越自信、越膨胀。只有比别人走得更高更远,才能看到更多风景。黄菊:也发现了更多新物种吧?徐波:这些年去了很多无人区,的确有很多新发现、有大量新记录。可能我走一趟,中国又多了几种植物,你说意义在哪里呢?问一个植物学家的工作意义在哪里,就像问生一个新生婴儿有什么意义,他可能是一个坏孩子,也可能是一个改变人类命运的孩子。标本采集也一样,发现两个新物种,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这是基础研究,一步步累积起来,任何一个物种都具备改变人类命运的基因和能力。系统的调查研究后得出一个植物名录,告诉世人青藏高原冰缘带有多少植物?它是怎么分布的?是怎么来的?哪些可以用?最终为植物开发保护提供本底资料。如果连家底都搞不清楚,又谈何保护和利用呢?而且高海拔地区的植物要活下来,需要挺过很多逆境胁迫:强烈的紫外线、剧烈的昼夜温差、不稳定的基质、极端寒旱,这实际上是一种战略资源,这些潜在的基因,未来可能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黄菊:本来一直想问,为什么牛羊都不吃我们拍的这些花草?人类这么热捧,学者也一直深究,难道就为了满足人类一点审美追求么?但刚才你说,这一切都是基础工作,也不知道哪天哪种植物就会拎出来,它们的作用会超越我们个体的生命,在几十、几百年后,像种子基因库一样发挥作用。徐波:基础研究就是这样,我们在写项目申请书的时候,都会说各种有意义,但研究植物,你说它能吃吗?还是能怎样?这需要时间来回答的。就像阿拉伯人驯化小麦,如果当时撸起来直接吃掉,可能人类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任何一个小小的举动、细微的知识积累,都可能改变人类命运。▲没有任何一片叶子、一朵花瓣、一种颜色、一种细微处的设计,没有经过精心设计,一切都恰到好处,极致环保、节约,又极致绚烂,这是高处生长的智慧。摄影/叶茂冷兆琦
日记·『在尾声,进入生命之旅』7.8难忘的一天,撞见个人旅行史上最大一次插曲、风波。已经出发离开的我们,折返回海拔米的卡久寺,在垂直落差千余米的羊肠小道上,狂跑了两小时。那也是当地人的外转经线路。无数个挥汗如雨的缝隙里,瞥见崖壁上,石缝里,今人为圣人的足迹献上的各种行宫。重要的不是圣人是否真的在此经停,重要的是今人为什么匍匐在地,愚公移山般,精卫填海般,献上一切,包括性命。越艰难的外在旅途,越能激荡出人内在的真实,在这趟告别之旅里,更加看清了生命这场旅行的道路。而我们折返,也一定是有非此不可的理由。这是卡久寺送给我们的礼物,各有领悟。7.9.面朝卡若拉冰川,我们爬上此次旅途最后一片流石滩。过去人们看待自然,都以有用、无用作取舍的标准,但自然文学作家利奥波德发明了一种他命名为“土地伦理”的新观念,提出,自然界所有生命都是自在的,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就像天下众生都是:“一云所雨,一雨所孕。”那天坐在高处,附身看见花友们继续匍匐在地,为了看见、拍到一朵植株矮小的植物,强风吹拂,鼻子一酸,我竟然哭了。高山花卉用她们的生命之光点燃流石滩,而面对花、面对流石滩、面对自然,我们究竟想要看到什么?又看见了、学到了什么?最终,我们又回赠了什么?“一云所雨、一雨所孕”,冰缘带植物利它、多样,共生共荣,我们俯身看见这一切,但转身面对人,又为什么立即重新变得逼仄、狭隘?转山转水千百回,转不出自我。而作为普通植物爱好者,多走一程路,多认识一种植物,究竟是使我们变得更加傲慢了,还是更为谦卑了?我常想起作家阿来的话:观花就是这样,需要适度地懂一点植物学,但当花成为一个审美的对象,比如现在,当一株满枝都是红色花蕾的垂丝海棠和一株盛开着白色花朵的西府海棠并立在一起相互辉映的时候,就应该忘记植物学了。但阿来接着讲到,“自然之神是从容自在的,并不那么急迫地要唤醒那么多人追随与服从,但我知道,我所以努力在靠近与体察,不是为了一种花,一棵树,而是意识到人本身也是自然之神创造的一个奇迹——也许是最伟大的奇迹,但终究只是奇迹之一,所以,作为人,更要努力体味自然之神创造出来的其它的种种奇迹。”每朵花都是奇迹,每种“杂草”也都是奇迹,如果像欣赏一朵花(杂草)那样欣赏一个人,已经没有几人值得我们驻足凝视了。我们更需要的,是为了抵达心灵的旷野,而翻越自我的高山和沼泽。▲卡久寺以她的一切,演绎着“仙境”二字。在海拔米的玛尼堆上,巴掌大的玛尼堆,周围密密匝匝地环绕着69株含苞待放的绿绒蒿。摄影/叶茂黄菊
『一生只读一本书』行李徐波黄菊:未来除了喜马拉雅北坡的行走计划,有写作计划吗?徐波:第一本书是《横断山高山冰缘带种子植物》,我本来想再慢慢把青藏高原的冰缘带做下来,出第二本书,然后再出一本绿绒蒿的书。出三本书,够了。但现在的科研也都是快节奏、快餐式的,我想慢慢做一辈子,但时代不允许,甚至随时可能出局。黄菊:全和青藏高原有关。徐老师平日喜好分明,也嫉恶如仇,但只要说起青藏高原,就柔软了下来。徐波:可能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一个东北孩子,却对这个区域从小就很向往,初中课本上就写着“青藏高原”、“喜马拉雅”这样的字眼,后来有幸接触到,一下子就离不开了。像上海广州这种大都市,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可以不去;有时也有经费可以去国外转转,我也没有去;我把所有的时间、经费和情感都花在了青藏高原和来去青藏高原的路上,毫无疑问这块土地在我心里的份量是最殊胜的。黄菊:我很感慨,随着游历、阅历的增加,年龄的渐长,人很容易有意无意间越来越傲慢,但总有一天会被某个东西收了,徐老师,还有我身边一些原本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狂人,最终都被青藏高原“收服”了。徐波:被青藏高原征服的人太多了,在自然面前,一切都非常渺小。大都市里那些复杂的东西,到了这里可以变得很简单、很纯粹,这些才是最真的东西,所以我对这里心存敬畏,也心存感激!虽然是外乡人,但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很深。我被青藏高原改变、塑造,最终也都心甘情愿且无比荣耀的成为高原的一部分。我不爱读书,我读的最后一本书就是青藏高原,这本书会读一辈子。「我读的最后一本书是青藏高原,这本书会读一辈子。」▲为了一睹芳容,我们可以不惧风险跋山涉水,可以不惜危险爬上悬崖,也可以不顾体面跪伏在地,但面对一朵花,我们真正看见了什么?无论如何,谢谢你们,和我们一起创造了这趟永生难忘的旅程。摄影/黄菊叶茂林森等
文字:黄菊
封面照:彭建生
照片鸣谢:徐波、彭建生、叶茂等所有同行者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