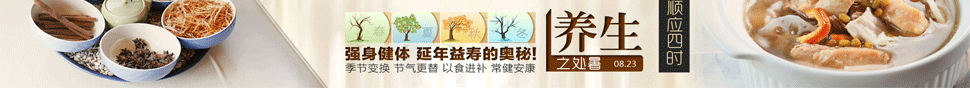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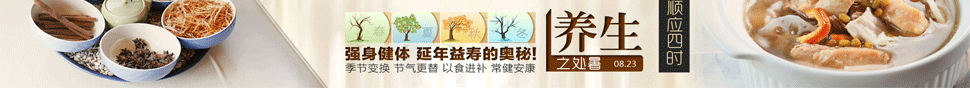
高村光太郎自画像
一
作为日本大正、昭和年代著名雕刻家与诗人,高村光太郎年(明治十六年)出生于东京,父亲高村光云是德川末期明治初期一名木雕师,后任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系职长,是当时日本声名远扬的雕刻家。高村光太郎是家中长子,在当时的观念中,自是要继承父业成为雕刻家。从小和父亲的弟子一起耳濡目染,也使他渐渐对雕刻产生兴趣。15岁时,高村光太郎考入东京美术学校预备科,开始专业学习,其后又进入研究科。这时他从蒙克莱克的书中知道了罗丹,开始对学校的雕刻教学产生怀疑,于是重新进入西洋画科学习。青年时期的叛逆、迷茫和彷徨慢慢出现,在学一年后,年高村光太郎退学,去到美国学习雕刻,这时他已经24岁。
在美国的一年半,高村光太郎在雕刻家伯格拉姆的工作室打工,同时参观美术馆,泡图书馆,观摩铜像,看剧,和在美国的日本艺术家聊天,这种生活滋养着剧烈成长的他。年他到英国,在美术学校和工艺学院学雕刻课,频繁出入于美术馆、画廊和图书馆,在街头观察流行趋势和艺术设计,观看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后来回顾起自己的这段留学生活,他说自己在美国的所得,可以说是摆脱了日本伦理观,但只是剥掉了身上粗糙的日本式外衣,而一年的伦敦生活,才让他沉浸在“西洋”醇厚的氛围里,感受到了“西洋”之魂。这是他在美国完全没感觉到的一种深厚的文化特质,他很快习惯了,并甘之如饴。
年,高村光太郎又去往巴黎进一步学习雕刻。作为世界艺术中心的巴黎使他感到更为丰富和自由,但不久之后,他对自己在巴黎的生活产生了怀疑,痛感自己无法抓住模特的本质,而想雕刻出心中熟知的日本人。在去意大利游览了一番之后,年他回到日本,结束了三年的留学生涯。
这时候,无论是在艺术追求还是在精神思想上,高村光太郎都已经和去国之前产生了巨大的不同。他成为一个自由蓬勃的年轻人,学会了认真思考、认真工作,受了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先进的知识滋养,一心希望在艺术的道路上更加刻苦精进。回到日本,父亲却提议以他为中心开设铜像公司,拓展铜像生意,令他感到十分震惊与失落。不久后,他在巴黎时结识的雕刻家荻原守卫猝然离世,也使他深受打击,感觉在日本再也没有说得上话的雕刻家。与此同时,在文学界,当时日本正掀起新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对抗的浪潮,年轻的创作者们蔑视世俗陈规,高村光太郎受其吸引,很快成为其中一员,以在巴黎过惯的生活为标准,对方方面面的旧体制展开攻击,写下许多批评文章,由此也招来不少嫉恨。艺术界的繁琐陈规与门户之见、利益之争使他厌恶,父亲引以为傲的头衔名声也让他反感,他拒绝参加文部省的艺术展览会,也不去拜访有权势的人,不跟古董商合作,父亲推荐的美校教授的职位也不接受,同时四处喝酒逸乐,成为亲友眼中不折不扣的“浪荡子”。
如此自绝于俗世,高村光太郎之后的道路自然不会平坦。雕刻出的作品无处发表,他的兴趣遂渐转移到油画上,和当时日本一些青年画家一起,希望以印象派的画风对抗日本当时白马会、太平洋画会的陈旧画风。他说服父亲,和弟弟一起在东京开了一家小画廊,陈设一些新人画家和他自己的作品,但是买画的人寥寥无几,几年后画廊也转手给了他人。因为完全不参加世人公认的各种展览会,自己在艺术上也得不到承认。他曾一度想去北海道做黄油养活自己的艺术,去参观后才明白光靠微薄的资本根本无法运作,只好继续回到东京,“就靠帮父亲的忙,像个手艺人一样领领工钱,每天喝喝烧酒,在‘潘之会’上发发酒疯,和女人乱搞,每天都找不到出路,徒然焦躁挣扎。只会端架子,和当时需要交际的艺术节越来越绝缘,只是成日和当时无名的年轻美术学生混在一起”,“我还是手头紧张,越是困顿越要喝酒……我不光是文学意味上的堕落,在生活上,也一步一步陷下去,脚步危险,精神上已经在吐血了”。(高村光太郎《我与父亲》,见《智惠子抄》)
年,在父亲帮助下,高村光太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建立了工作室,开始搬过去一个人生活,每天回一次父母家。环境的改变让他恢复了些许勇气,他一边继续帮父亲做活,一边接了大量翻译工作。也差不多同时,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长沼智惠子,两人很快产生感情,智惠子身上纯真清新的气息,使光太郎彻底从之前的颓废中走了出来。智惠子是福岛县二本松一个酿酒商家的长女,在日本女子大学读书时喜欢上画画,毕业后在东京太平洋画会学画画,曾为当时的女性主义杂志《青鞜》绘制封面。他们的感情不为光太郎的父母所同意,也引来熟人的流言蜚语,两人备感压力,然而还是坚持下来。年,高村光太郎与智惠子结婚,放弃了家中一切土地房屋等财产,和智惠子在工作室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高村光太郎与长沼智惠子
两人潜心于艺术创作和学习,经历了很长一段贫穷的生活,直到年,已经41岁的高村光太郎重新开始制作木雕,获得了父亲的赞赏,也获得了世间的承认,可以依此拿到收入,虽然仍不稳定。然而,因为长久的不得不应对贫穷的日常生活和自己在艺术上的追求无法实现的痛苦,以及深爱的娘家的破产,年,智惠子的精神逐渐出现问题。年智惠子疾病恶化,此后不得不辗转于精神病院、老家和疗养院,年,智惠子去世,从此高村光太郎终身孑然。
二
我在冬天的寒夜里读完高村光太郎的《山之四季》,回过头去寻找关于他的更多资料,在他为智惠子所写的诗集《智惠子抄》中读到他从青年到中年时期所经历的漫长的,几乎充满挫折与反叛的贫穷、挣扎的生活,不禁感到深深的意外和震惊。在《山之四季》这本作者晚年沉静而优美的散文面前,很难想象背后曾是那样一个坚定反抗世俗的灵魂,以及这灵魂也曾走过的幽暗歧途。智惠子去世后,高村光太郎一度失去创作的动力与目标,从前他每完成一个作品,都会第一个拿给智惠子欣赏,最爱它们的也是智惠子,从那以后却不会再有了。直到后来,他认为智惠子虽然已不在人世,对他来说却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永恒存在,才又平静下来。
高村光太郎的雕刻作品“文鸟”,智惠子生前很喜欢,经常携在怀里
“二战”期间,高村光太郎担任了日本“文人报国会”的诗歌部部长,写下了一批赞美侵略战争的诗歌。年,日本战败后,高村光太郎受到严厉批判,自己也为从前所犯下的错误感到巨大的震撼和痛苦。他在东京的家为战火摧毁,搬到花卷的宫泽贤治家借住后不久,宫泽家也被炸毁,最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去到日本北部的岩手县山口村寄居。
在当时的日本,高村光太郎这样的人被称为“疏散人群”,即所居住的城市被战火毁坏,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生活,等返回的条件成熟,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居住。因此高村光太郎刚到山口村时,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最初村民帮他搭建小屋,他觉得只要撑够两三年就可以了。后来因为太过简陋,又重建了一个,实际也仍然非常简陋。住久之后,他渐渐萌生出在这里长住下去的想法,最后在那里居住了七年。《山之四季》正是他七年山居生活的概括,全书记录了山村四季的风景、食物、动物、植物,以及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
山中小屋
如村名所示,山口村位于田野尽头、山的入口,从那往后便是奥羽地区连绵的山脉。高村光太郎的小屋靠近山边,离村子四百多米,周围除了树林、原野和少许田地以外,没有一户人家,在岑寂的山中,要更多一重寂寞了。这本书适合在寒冷的冬夜,独自守在温暖角落,就着滚烫的茶边看边喝。因其质地轻盈而沉静,开首便是冬天被大雪深覆的山中独居的生活。这里属于日本东北,气候寒冷,冬日漫长,每年十一月就开始下雪,冬季原野上一望无际厚厚的积雪,每隔一阵子,人们就要把屋顶上的积雪扫掉,以防大雪把屋子压垮。高村光太郎写大雪包围下一个人的生活,充满极端的寂静与寂寞。“每到积雪的时节,四面都是白雪,连个人影也见不着。人声、脚步声,自然也是听不见的。不像下雨,下雪是没有声音的,每到这时,待在屋里,感受着悄然无声的世界,便觉得自己像聋了一般。尽管如此,偶尔还是能听见地炉里柴火毕剥的响声,以及水壶里热水沸腾的微弱声音。这样的日子将一直持续到三月。”这样的冬日,他整天坐在地炉边上,边烤火边吃饭,或是读书、工作,“一个人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也想见见别的人。就算不是人类,只要是活着的生物,飞禽走兽都可以”。因此附近任何生物的动静都会留意到,窗外啄木鸟的声音,清晨和傍晚飞来屋檐下啄食菜籽的不知名的小鸟,夜里跑到榻榻米上和人抢面包的老鼠,还有每一种动物留下的脚印。他甚至能分辨出雪地上每一个人的足迹,无论是穿着什么样的鞋子,因为每个人走路的姿势不一样,看到脚印就大概能猜出这是村子里的谁。
“狐狸的脚印”
种种细节,都是珍贵而真切的实际体验,不是曾真正在大雪封闭的山中久住过的人,绝不会有那样生动细致的观察。写这本书时,高村光太郎已在山口村居住了五年,逐渐融入本地人的生活,对于那里的山川自然也已经非常熟悉,写四时的变化以及人依附于此的种种劳作与生活,充满久住的在地人的熟稔,是历历在目的真实的细节。不是匆匆到此一游的旅客,也不是一个精神上游离在外的“疏散者”的视野,而是一个真正理解了当地村民和他们的生活、与背后的自然共生的“真正生活者”。他对山中的动植物充满兴趣,对四季变化的规律和征兆也观察得细微而准确,了熟于心。他写山中的春天,最先来临的标志并不是积雪融化、草木发芽,而是屋檐下忽然挂上了许多冰柱。因为只有到了初春,天气变暖,雪才会稍稍融化,滴下屋檐的过程中又被冻住,从而形成巨大的冰柱,这样的冰柱,在极寒天气里反而不会出现。又如写山中的夏秋,所有植物都抓紧从初春到夏季的土用(入伏前十八天)这段时间,拼命生长,散发出的强烈生命力,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然而一到了八月盂兰盆节,“原来那声嘶力竭般的气势霎时就消退了……山野间不知为何突然间就安静了下来。不同季节中植物的生长规律简直严苛到了让害怕的地步,植物们总在争取着每一天,甚至每一刻”。这样精确的观察,读来令人赞叹。
山中生活贫瘠,高村光太郎写及自然,也念念不忘四季的吃食。春天是山上的野菜:放在金属丝网上烤一烤,刷上味噌,蘸上醋,再滴一点油,吃起来味道微苦的款冬;油炒一下就着糖醋酱吃的千叶萱草;从春腌渍到冬,正月里才吃的青翠的盐渍蕨菜;将嫩叶煮熟拌上胡麻和核桃来吃的轮叶沙参……虽然都很简单,但看着也都觉得很美味似的,大概因为其间有一种珍惜的情感在。秋天盂兰盆节前后,村里人会做红豆年糕和鲣鱼片相赠,也会聚在一起喝米酒、吃荞麦面。他很喜欢地方的米酒,喜欢一个人坐在地炉旁,用茶碗静静品味,觉得简直没有比这更舒心的事了。秋天山野里可以捡栗子和采蘑菇,都是贫寒的生活里偶尔发光的点缀,因而格外显得温情与美好。
同时身为艺术家与诗人的细致与敏锐,使得他的散文语言朴素、清洁而刚健。《山之四季》薄薄一册中,主要篇目如《山之雪》《山之春》《山之秋》《山之人》《陆奥的音讯》,许许多多段落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美妙随手可掇(另外一些篇目,写的时间似乎早一些,有些作于刚到山口村不久,更像是日常生活较为松散的记录,不及主要篇目的结构完整,富于整饬、概括与丰富之美)。作者对自然的观察与鉴赏,其品味也十分高雅,那些山川原野四季中优美的时刻,他能真正懂得欣赏,沉入其中。春天与秋天美丽的晚霞,秋天夜晚澄澈的天空与皎洁的月光,冬天夜空中大得怕人的星星,以及原野上广阔的平原,山间繁茂的树木,远处起伏的群山,四季的植物与动物,也需要有能够察觉它们的眼睛。也因此,这些文字对读者并不是没有要求的,倘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无所用心,读起来大约就很难体会到那背后广阔世界的动人。
三
然而书的背后,还是有着山村生活艰难的背景,以及作者对自己“二战”中错误思想的痛苦反省。生活在那里的人,实际上是相当不自由而辛苦的。因为土地贫瘠,山口村的村民要更加辛勤地劳作,才能够保证基本的生活。夏秋在田间耕作,冬天则进到山林中砍柴烧炭,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少有休息的时刻。高村光太郎在那里的生活也十分艰辛,木屋狭小简陋,只勉强可供一人起居,墙壁只有一层木板,冬天可供取暖的,不过是一个做饭的小小的地炉,在那样高纬度的地区,可以想象其寒冷。几年后才有了电,没有自来水,村民在门口为他掘了一口井。更困难的则是战后粮食短缺,有时连分配的米也很难拿到,村里人有时拿一点米,或是萝卜、土豆、咸菜之类的东西,让小孩子来送给他,就这样异常艰难地,熬过了头两年的饥饿和严寒,活了下来。几年之后,他回想起初来山村时严冬的情形,写道:“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平米小屋中间,点起地炉的火,看着窗外积雪三尺的景色,便不由得想起日莲上人被流放到佐渡岛,在塚原的一间庵室里被雪掩埋的故事。”这并非夸张的言语,而是生活真实的写照。
高村光太郎在小屋,电灯是住进去两三年以后才有的
他也努力适应自己种地、自给自足的生活。为了解决食物问题,他在木屋周围开垦了小块田地,在上面种植了许多蔬菜。这对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他来说,实在是非常劳累的工作。余下的时间里高村光太郎也没有停止文学创作。身体长期的营养不良、寒冷和繁重的劳作,最终引起了肋膜炎和肺结核,有一两年夏季,他不得不放弃了耕作,任由杂草将蔬菜淹没,勉强获得一点收成。事实上,回到东京没几年后,他就因为山中埋下病根的肺结核去世了。
另一方面,他也在书中提到自己在“二战”时所犯的错误,给他精神上带来持续的痛苦。“一呼吸就疼的肋间神经造成的痛苦,和一说话就疼的精神深处带来的痛苦,两者是相呼应的。”(《陆奥的音讯》)在他搬来之前,附近还有另外一个富裕些的村子可以去,然而他还是选择了这个土壤更为贫瘠、人们也更加辛苦的村子,这其间大约有一种自我救赎的意味在。这不是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隐居”,它并非出于避世,而与他自己一生所选择的真挚的道路相一致。“虚伪与懒惰无法存活于这里的土壤,/我像自然那样,争分夺秒,/赤身裸体,埋头向前。”(《都市》)山口村的人几乎原始的、如牛马般辛劳的生活,被外人认为是不卫生、无知、狭隘的,高村光太郎却能看到他们纯真朴实的一面,认识到正是生活条件的艰难,使他们保持了淳朴的民风,形成了互帮互助的习惯。居住渐久之后,他也更加理解了村民那种几乎“不讲礼”的耿直与不虚伪,而不是以都市人的思维方式贸然加以判断。他也试着逐渐“浸润”到村民中去,参加村民的例行聚会,和他们谈论真实的山村生活,以及“日本的复兴”,“美与道德”。“我敬爱村里的长老,也爱护村里的年轻人。自己不懂的事就向村里人请教;每每学到新的知识,一有机会就向村里人转达。”从未把自己当作置身事外的人过。
因此,看了这样的文章,就随随便便说着“也想住到山里去隐居”之类的话,无疑是不负责任的。既未曾理解作者山居的艰辛与孤独,对自然的想象也过于舒适和浪漫化了。而实际上,即使是在生活条件大大优越和便利了的现在,真正生活在自然,尤其是在那样严寒地方的自然中,也是十分辛苦和严酷的。别的不说,光是大雪封山几个月那种无边的寂寞,又有几个人能承受呢?
四
高村光太郎选择在山间久居,和妻子智惠子也有一定的关系。光太郎对智惠子的爱情,一生未曾改变,《智惠子抄》是两人从相恋到死别的诗歌编年史,晚年住在山间,高村光太郎仍旧写了许多给智惠子的诗。智惠子生于陆奥的福岛县,从小在乡下自然中长大,本能地热爱自然,《智惠子抄》中有一首《天真的话》,讲述智惠子曾对他说起“东京的天空不算天空”的话:
智惠子说东京没有天空,
想看看真正的天空。
我吃惊抬头看天。
樱花嫩叶间,
是从小见惯
划也划不破的,一片晴空。
模糊的地平线沉淀着
清晨浅桃红的雾气。
智惠子看着远方说,
阿多多罗山上
每天出现的蔚蓝天空
才是智惠子真正的天空。
这真是关于天空,天真的话。
长沼智惠子
思念乡下心切的智惠子,待在东京就经常生病,回到娘家就恢复健康,因此一年中他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乡下度过。智惠子去世后,高村光太郎在纪念她的《智惠子的半生》中曾哀痛地反省,“我出生于东京,也在东京长大,她这伤感的倾诉,我无法感同身受,一直以为,总有一天她会习惯这个大城市,但她对新鲜而透明的自然的依赖终其一生也不曾改变”,认为这是“她半生中未曾明说的幽怨”。晚年高村光太郎住在山间,也怀着一种对智惠子的纪念与补偿的复杂心理。松浦弥太郎在《日日》中写到,高村光太郎晚年在山间,每当感到孤单时,就会爬上视野良好的山腰,大声喊:“智惠子——智惠子——”在山中居留的七年,高村光太郎写下给智惠子的《假如智惠子》《元素智惠子》《都市》《向导》等诗篇,“智惠子死了又活,/她寄生于我的血肉,/被山川草木包围,欢欣雀跃。”(《都市》)想到与他的精神同在的智惠子,生活在这里,应当也是很高兴的吧。《向导》一诗中,如同智惠子就在身边一般向她介绍山居生活的情况,读来哀意宛然:
有三铺席大小就能睡个好觉。
厨房在这儿。
水井在这儿。
山里的水跟山里的空气一样清甜。
田有三亩,
今年白菜丰收了。
那边是稀稀疏疏的赤杨林,
围着小屋全是栗树和松树。
爬上山坡视野开阔。
南望二十里一览无余。
左边是北上山系,
右边是奥羽国境山脉,
北上川纵贯中间的平原
那云霞缭绕的山峰,
就叫金华山冲吧。
智惠子中意吗?智惠子喜欢吗?
曾经充满年轻的意气与才华的智惠子,有相互理解和共同追求艺术的丈夫,在实现自我的途路中,最终尚且陷于家庭生活的艰难与自我怀疑的痛苦,使人不得不感慨那个时代的女性,想要实现独立的自我价值,所经历的路途之艰难。这种艰难,到如今大约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改变。精神分裂后,智惠子在病院中一度以剪纸创作自娱,《山之四季》中也写到去参加智惠子的剪纸遗作展的事情。智惠子一生以油画为创作目标,因为达不到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而备感痛苦,最后却仍是依赖丈夫纪念她的诗集而为人所知。《智惠子抄》的中译本里有几张她的剪纸遗作,但想多看几张也不可得,这样的际遇,实在令人唏嘘。
智惠子的剪纸作品
五
小森的木屋
年,森淳一导演的《小森林》上映,在中国也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电影拍摄于岩手县的奥州市衣川区,离《山之四季》中所写的地方不远,讲述了在小森长大的市子,从城市归来在乡下重新居住了一年的故事。电影着重所展现的,是她一年山居生活的劳作与吃食。电影中靠山的独立小屋,以及春天上山寻找野菜做成食物(一些野菜野花的种类也颇相同),晚上听见附近动物的动静,菜地里种植的蔬菜,夏天做完农活后一口气喝掉的白色米酒,秋天树林中的栗子,小孩子喜欢爬到树上去摘来吃的八月炸胖胖的、淡紫色的果子(书里译成“野木瓜”),一根根竖立在田中、捆绑收割好的稻子的木条,大雪之后爬上屋顶铲雪,春天快要来临时溪水边出现的冰凌,很多细节的安排与设置,无疑是受了《山之四季》很大的影响与启发。
这是什么花我忘记了,呵呵,但是感觉书里提过
小森里市子酿的酸米酒。冬天写这篇时,就变得很想喝米酒,网上买了有十瓶,夜里一杯接一杯喝。还试着做了这种酸米酒,真的太酸了,最后全倒掉了,呵呵
和《山之四季》里描写的一样的收割稻子的方式
八月炸,小孩子们会爬到树上摘
尤其是栗子,电影中,市子在风吹飒飒的金黄树林中捡拾栗子,一只鸟扑翅飞起,让人以为是灰熊,吓了一跳。这和书中说“人们为了捡栗子,常常进到山林深处去。时不时碰上熊出没的痕迹,就飞也似地逃回来了”简直一模一样。《山之秋》一篇里,有一大段关于捡栗子的优美描写:
“白天的时候还有点热,但早晨的空气是很清爽的,甚至略有点寒意。早上,我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从门口走出去,就能看见地上骨碌碌地滚动着掉下来的栗子。刚掉落不久的栗子色泽十分美丽,有种干净的感觉,特别是尾部那一溜分明的白色,简直就像还保持着生命一般。潮湿的地上四处散落着黑色和褐色的栗子,两种颜色互相交织,给人一种高雅的感受。开始捡栗子以后,发现目光所到之处全都是,连茂密的韭菜丛中、菊花的背阴面、芒草的根部都有栗子闪着光亮。我每天早上都能捡满满一箩筐,剩下捡不完的就放任不管了。捡的过程中也不断有栗子从树上掉落,砸在我的屋顶上,那声音出人意料的大。熊竹丛中也沙沙掉落了许多栗子,但掉在这种低矮灌木丛中的栗子隐藏得很好,几乎找不到它们的踪迹。”
电影里掉在地上的板栗
读过书后,再去重看电影,无论对书和电影,都有更深一重的认识。电影中大山上繁茂的植物,盆地间低洼的田地,秋天无数金黄的树林,绵延的晚霞,无处不在的动物的声音,都使人如见书中描绘的风景,更添一份亲切。只是隔了六十年的时光,现代化社会各种机械的发明,毕竟减少了很多从前的辛苦,电影拍摄又多少使之浪漫化,但是两者中还是有隐隐一贯的精神。年,高村光太郎面对山口村春天的山花,想起年轻时在帕多瓦旅行时所见的梨花,以及那里深厚的文化,希望山口村也终将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到了森淳一导演《小森林》的时代,小森仍然是日本相对传统、原始的地带,地方人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四季在农田与山中劳作。只是社会早已发生巨变,年轻人纷纷离开凋弊的农村,小森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电影中导演借市子之口,问收割稻田时给她送来水果的一直住在小森的吉子奶奶:“我不在小森的时候,奶奶每年也都插秧割稻捡核桃吗?”
吉子奶奶回答:“是啊,小市没出生时就这样子。年年都这样,哈哈哈哈。”
可以说是对农业生活的一种温和的肯定,是伸出手来,给予年轻人以自然的邀请——祖辈的人还是倚在这大山环绕的环境之中,如同背后的山脉和田野,如同山中的野兽与植物,扎实生活于此的。剧中的市子回到小森一两年之后,又离开重新去到城市,生活了五年,确定自己并不是将这里当作自己失败的逃避之所,最后带着丈夫重新回到小森生活,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从前的学校组织起第一届“春收节”,并表演了地方久已不复的儿童神舞,“借此机会,说不定又有人愿意回小森了呢”,虽然不是现实,却也是一种温柔的、美好的、也许不无虚幻的寄托(现实中,拍摄这一场景的旧学校仍然关闭着)。在高村光太郎去世几十年后,还有人和他对这片土地怀着同样的希望其形成、保留其朴素独特的文化的愿望,并发力将这愿望使更多人看到,也是一件令人可感的事。至于高村光太郎本人,则在山中居住七年之后,回到东京,不过几年,便因为在山中已出现征兆的肺结核病去世——是和他挚爱的智惠子相同的去世病因,使人惋惜的同时,也感叹命运的奇异的。
春
夏
秋
冬
注:文中所引高村光太郎诗歌,均引自高村光太郎《智惠子抄》,安素译,中信出版集团年6月版
又及:这本书的翻译感觉有不少知识性错误,书里的“八葵”,一会译作款冬,后面却又变成了忍冬(这里编辑也要负责任),还有一篇里几次说收获稗子,我还从没有听说过哪里把稗子当农作物收获的……《山之秋》那篇里,说“七月,田地里的稻穗渐渐发芽了”,估计作者说的其实是稻穗逐渐长出来,灌浆了吧。还有《山之雪》那一篇里,说“走路时喜欢把鞋子的后跟弯曲的人走起来似乎也不轻松。这是因为身体弯曲的人,心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实在使人难以理解,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一段别人翻译的这篇的节译,就能看懂,但是忘记存下来,现在又找不到了:)
随意哦~
沈书枝给枝枝打钱买米酒!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jintiesuoa.com/jtstx/7508.html

